首页 > 新闻 > 书坛快报 / 正文
书之旅——访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获得者 张荣庆
■本报记者 叶积艳

张荣庆 1938年出生,河北安国人。曾任中国书协研究部主任、学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二届理事,中国美术馆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清华美院客座教授。组织策划第二至五届全国书学讨论会等多次重大书法学术活动。潜心于古代书史书论研究兼及书法评论等,有文集《退楼丛稿》行世。
书法报:张先生,您好!恭喜您获得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此次获奖有何感想?
张荣庆:之前我已写过一些感言,见《书法报》2013年1月2日第7版及中国书协出版的第四届兰亭奖作品集。在这里,我再补充一点感想,就是如何对待获奖?因为这个奖重要,说毫不在意是瞎话,参与了就是在意,在意一点也无可厚非。但太拿它当回事,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获奖”,并不意味你的书艺到顶了,成大气候了。历史是最公正的过滤器。若干年后,谁还理会你拿过什么奖?所以千万不可晕头转向,忘了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把自己建设好是最切实最重要的。
书法报:您是学建筑出身,后又做编辑,再转到中国书协工作,跨度较大,能介绍一下您的学书经历吗?
张荣庆:把并非不喜欢的专业及从事多年的建筑设计工作舍掉,转而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干了几年编辑,又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最后落脚到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我的跳槽跨度确实是够大的。但细细思量,大概终究还是久积于内心的一种潜意识的力量——从小就养成的对写字的特别钟爱使然罢。
然而从实际情形看,我的学书,早先是完全不懂的,到多少悟出一些道理而逐见增进,经历的过程很长。自觉稍微上点道,大抵始于1989年。此时我已50岁开外,同许多活跃于当今书坛的年轻尖子们相比,我差远了,的确属脑子很笨开窍甚晚者。这年的8月,中国书协举办全国第四届书法篆刻展,且是首次设奖,评出50位,我的一件六尺整纸行草书,居然获得三等奖(此后各届不再分一二三等奖)。1989年11月,还冒然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个人书法展。1992年夏,复得两项奖:一是第四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二是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展。现在回头看,那时写的字,毛病太多,太嫩,实在不堪入目了。
尽管很不好,我的学书却由此得一大契机——我坚持“入古”的学书理念(或谓学书方向、学书取径),乃于那时明确地树立起来。我的“入古”,顾名思义,就是力学古人,古人里头,二王境界最高,故二王书法一直是我追踪的至高标的和书风取向的基调。重点是学古人,今人当中学古人学得好的,我也学。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入古。我把我的学书之路因而命之曰“入古之旅”。2008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办第二次个展,就取了“入古之旅”这样一个展名。
学书路径之确定乃至取法之抉择,固依性情之所近,但更重要的前提,我以为当对书法的历史有所知晓。20世纪80年代初我买来一本潘伯鹰先生著的《中国书法简论》(增订本),读后使我受益匪浅。此书不厚,史论、技法兼备,文图并茂,笔致清畅,钟王以下历代重要书家评传,写得尤其精彩。读了这本书,在我头脑中,自古至今关于二王帖系书法的脉络就比较清楚了;了解了东晋以降历代书家盖无一不受二王滋乳,从而对二王的崇高书史地位,也建立起充分的认识。同时对篆隶北碑这一大块,也理出一个大致的头绪来,明其源流,辨其优劣。就学书取法而言,我便立定以二王为主宗,历代诸家连同碑版在内,凡是我喜欢的觉得好的尽可上下左右任意撷取,化为己有。同时还推荐另一套内容扎实而丰富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朱关田、丛文俊、曹宝麟等七人分撰,江苏教育出版社)。
要了解书法史(含古代书论及经典碑帖),还要看很多的书,这使我对古人学书得以成功的必由之路,有了一个明确的认知。学书必须要字内功夫和字外功夫双管齐下。古代大家作书,率皆洞明书理,法度精微完备,且极通变之能事。加上他们又都是很有学问的,炼字和学养之积累,最终归结为修心。古人是把修心视作比炼字更为重要的。修心到什么程度?修到佛家所讲的平常心,修到冲和清静,修到大自在,进入大光明界,那就高了。
在学书过程中,我对感兴趣的书家,着意尽量搜集与其相关的史料,作全面深入地考察。比如王羲之,我从史书、笔记、类书中广泛搜集唐前有关他的传记史料以及当时和后世对他的评价资料,又读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想象中的王羲之的样子,便活现出来。我觉得这样学《兰亭序》、《圣教序》,比死啃字帖而对王羲之毫无所知,要好得多。前些年曾对杨凝式的《韭花帖》特别着迷,我亦采取此法。近期写小楷,尤于《十三行》深有体味,也是靠了平时积累的有关王献之及其《十三行》之大量资料而得补益的。我以为这个办法,既是学书不可少的基本功夫,同时也等于是做学术研究。我的一些书学研究论文,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平时读帖多于临帖。《兰亭序》、《圣教序》是我最为倾心的学书范本。但前者临过有限次数,多非刻意摹写,取其大意而已;后者迄今尚未通临一遍。两本帖子经常反反复复看,每次看都有新鲜感。我还精读过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李邕、张旭、颜真卿、杨凝式以及苏、黄、米、赵、董等书家作品。抻出一本帖来,把玩半天半宿,是常有的事。观其结字、用笔、用墨以及章法布局上的独到之处,并深入到极细微的地方反复琢磨。一个帖,今天看,觉得不错,就吸收一点。过些日子再看,又有新体会,就再吸收一点。如此这般,东拿一点,西拿一点,迄无休止。有时兴致来了,便舒纸提笔划拉一通,写它一段。有时看中帖上某字有意思,想把它学来,于是猛练无数遍,直至觉得差不多行了为止。总之,我这个学书办法,不成体统,赶不上好多朋友临帖所下功夫之深,但我觉得也有点好处,那就是通过长期读帖,在优游消遣亦即一种玩的状态之下,不用费力而能获益。黄山谷就说过:“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又谓:“凡作字须熟视魏晋人书,会之于心,自得古人笔法也。”由此看来,古贤也颇以为此法不坏。
书法报:时下学二王的人不少,但人谓“千人一面”。您也学二王,能否谈谈您写二王的体会?
张荣庆:近年来的书坛创作,回归传统经典的大趋势,很好;写帖一路的,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作者,“取法乎上”,直追二王,也很好。一个个把二王的字抠得很像,作品中直接搬用。时下展览多,大家都那么弄,集体无意识,遂造成“千人一面”的局面。单看一件作品,你也不能说不好,可是凑到一块,风格面目雷同。
如果我们观照一下古时成大气候的书家,情况便大不同。明代谢肇淛《五杂俎》有一段论书云:
王未尝不学钟也,欧、虞、褚、薛以至松雪,未尝不学王也,而分流异派,其后各成一家。至于分数之不相及,则一由世代之升降,二由资性之有限,不可强也。即使可强而同,诸君子不为也。千古悠悠,此意谁能解者?
王学钟而迥异于钟,欧、虞、褚、薛、赵,都学王而皆自成格局。倘让他们死照王字样子写,他们是能做到的,然而“诸君子不为也”,他们不愿那样干,他们终于都站住了。
我以为眼下学二王的全国展入展作者甚至获奖作者,大多尚徘徊矜能于形似的摹拟状态,做深做细的字内功夫还不及古人,字外学养和心态修炼则更是远远赶不上古人。这话或许说重了一点,但严峻的现实不容不发人深思。解决之途径,我意还是须要字内字外双修,要有办法超越摹拟,总揽笼络,脱胎换骨,在古人的夹缝中趟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各有奇招,相互之间自然就拉大距离了。这事不能着急,要慢慢解决。时下好多朋友拿写字参展当上战场,动辄不是打拼就是冲刺,火药味太冲,我看不好。心静不下来,书看不进去,老这样折腾下去,于事无补。
书法报:自2004年起,您每年坚持举办上巳节(农历三月三)雅集,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荣庆:今年的4月20日,刚在北京举办了“癸巳上巳·妙乐雅集”,由我牵头组织的“上巳雅集”,这是第10次了。
此项雅集活动,发端于2004年5月的“华宝雅集”,同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北京二十二人书法展。当时,非官方的影响大的书法联展还极少,尤其这次颇具规模和档次的纯民间性的雅集活动实属首倡,所以一亮相便在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此后,每年大体在农历三月三这个日子举行的“上巳雅集”,遂成定例。“华宝雅集”是由我和薛夫彬、周志高三人共同发起策划的。后来的雅集,薛、周二先生不大参与了,一直由我牵头坚持下来,这一点不可掠人之美,必须说明的。
雅集,其实说白了就是忙中偷闲,众人凑到一起玩。历代文人雅集,史不绝书。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三,大书法家王羲之邀集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二位友人,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之兰亭举行修禊活动,这是历史上玩得最漂亮的一次文人雅集。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在一种非常欣快的状态下挥写完成的。此后历代文人雅集,特别是上巳节三月三的雅集,多受“兰亭雅集”之启发。我们的雅集,其初衷便多少带有一点向往接续的意思。邀集一些书界的朋友在一起玩一玩,大家很高兴。我们的玩,是讲情趣,讲品位,讲境界的。我们的雅集一直坚持的宗旨是:致力于“兰亭精神”的弘扬光大,共同营造一种平等、宽松而和谐的氛围——不论职位高低,少长平起平坐,相与游处,澄心论道,切磋艺事,补短取长。
书法报:您“读书上瘾,藏书成癖”。曾因藏书突破万册而被评为“北京市家庭藏书明星”,您收藏的主要是哪些书?可否向书法读者推荐一些?
张荣庆:我的书很杂,大体说来,多属社会科学中的文史类书。倘按古代图书分类,则经、史、子、集都有一些。
首先是史书。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我备有两套,另有一部《清史稿》。《二十四史》称为正史,里头有很多书家材料。正史之外,还有许多相关史书,如编年史类、别史类、地志类、政书类(讲制度的)、姓氏类、金石类、目录类书,重要的能见到的尽量多买。
古代类书相当于今天的百科全书,里面书法材料非常丰富,重要者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事类赋注》、《玉海》、《永乐大典》(残存本汇辑)等,我手头都有。
我读书喜杂览,亦想顺手捕捉一些书法资料,历代笔记则正合我意。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50余种)、《元明史料笔记丛刊》(25种)、《清代史料笔记丛刊》(44种)以及《学术笔记丛刊》等,我基本购齐。大象出版社《全宋笔记》(每辑十册,含笔记多种),已购三辑。集部中的丛书,因含笔记书多,故见到即买,已有《儒学警悟》、《百川学海》(线装五函)、《说郛三种》、《汉魏丛书》、《学津讨原》、《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古逸丛书》等。
与书法直接有关的艺术类书,单本如《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等很多,还有《四库艺术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美术丛书》以及《书画书录解题》、《中国书画全书》、《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尚缺三册)等。
经部书如《十三经注疏》(属儒家经典),子部中的先秦两汉诸子书如《老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是中华文化的源头;还有佛、道“二氏”书;这些跟古代书家思想有关系的书,我都有点。
我的集部书,一是总集,有《昭明文选》、《乐府诗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以及《全宋诗话总编》、《全明诗话总编》、《词话丛编》等。二是历代诗人、学者、书家专集、年谱等,我有不少。比如我喜欢陶渊明,陶集和他的年谱,有数种;苏东坡诗、文、词集及年谱都有。
我所存还有许多近现代学人的文集专著,如《王国维遗书》、《饮冰室合集》、《弘一大师全集》、《鲁迅大全集》、《周作人自选集》、《胡适文存》、《陈寅恪集》、《钱锺书集》、《顾颉刚全集》、《周一良集》、《周振甫集》、《宗白华集》、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等。欧美、日本及港台地区学人著述也有一些。
此外,跟书法有关的考古学、简帛学、敦煌学、民俗学、文字学、史源学、考据学、校雠学、辑佚学、版本学(含藏书题跋、书话等)以及大型辞书、索引之类的书也有不少。
我所读的书,文言文的古籍很多。我大体能过文言文这一关,是在上高中时,借读班上同学一部《聊斋志异》,天天啃,当故事看,不知不觉解决的。后来读知堂(周作人)先生一篇短文,原来他小时候上私塾,也是通过偷看《聊斋》,才慢慢能看懂文言文的。有兴趣想排除这个拦路虎的年轻朋友,此法不妨一试。
书法报:您手头上还有什么工作(或创作)正在进行?今后有什么打算?
张荣庆:对我来说,持之以恒正在进行的“工作”,无过于读书了。我记性不济,很羡慕那些读书过目不忘的人;又不会使唤电脑,看书当中遇到有用的材料,还是传统的老办法,随手抄录。
今后没有宏大的计划。抄书当中列了不少可资研究的大小题目,但形成文字者甚少。想抽时间写点文章,但写些什么也没个准主意。出去走走,办班或展览,常有朋友相邀,看情况,可行就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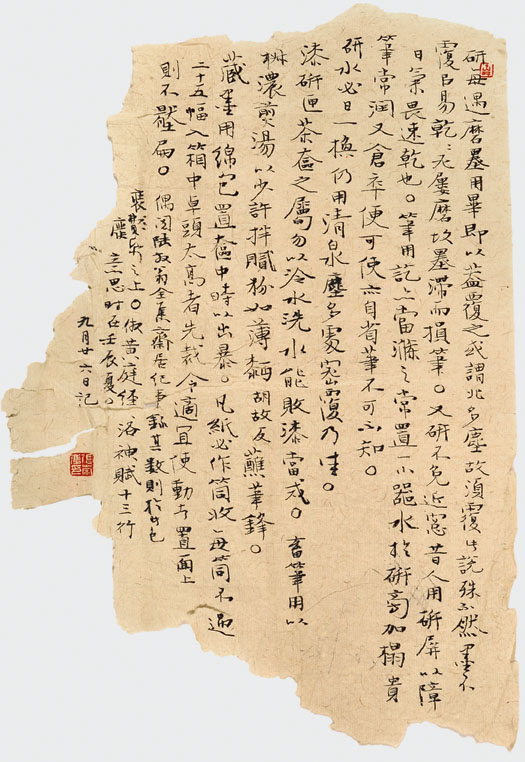
猜你喜欢
- 2015-03-17 邱振中:探索书法的可能性
- 2015-03-17 中国在全球艺术市场的份额继续回落
- 2015-03-17 沈阳故宫首次展出86件中国古代铜镜
- 2015-03-17 中国画都·潍坊艺术百家学术邀请展
- 2015-03-17 继往开来——2015中国版画家邀请展
- 2015-03-17 沈阳故宫首次展出86件中国古代铜镜
- 2015-03-17 民间收藏者现日本旧地图 证明钓鱼岛非日属
- 2015-03-17 盘点世界收藏界的中国风(图)
- 2015-03-17 行家称红木家具收藏未来热点是酸枝
- 2015-03-16 兰亭何为:兰亭奖评审的尺度与标杆
- 搜索
-
- 11-16《CCCPA全国少儿书画艺术等级评定简章》发布 2017春季开始报名了
- 09-302016第九届(国际)青少年儿童书画交流大赛火热征稿中(图)
- 01-05福州:俏笔迎春 助学公益
- 12-19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及理事名单
- 06-10书法家吕庆宜在福师大美院开展艺术讲座
- 04-18全国第二届手卷书法作品展获奖入展公示名单
- 04-13《中国书法报》创刊并面世
- 04-13辽报集团注资合作 中国书法报社在京揭牌
- 04-13《中国书法报》创刊: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 引领书坛
- 03-25福建省老艺协书法委员会在省老干局召开会议
- 16179℃周志高执掌《中国书法》大印
- 11964℃免费赠阅《炎 黄 书 画 报》
- 11046℃刘荣升书法作品选登
- 10139℃中国榜书名家精品展揭晓
- 9846℃中日当代书法大展开幕
- 9781℃韩国直指书法大赛圆满落幕(附获奖名单)
- 9072℃首届中国榜书大赛获得名次暨优秀作品名单
- 8841℃丘程光将在大连举行书法展
- 8647℃中国天津/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 8192℃ 第二届国际榜书大赛暨中国榜书艺术大论坛揭晓
- 01-05福州:俏笔迎春 助学公益
- 12-19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及理事名单
- 06-10书法家吕庆宜在福师大美院开展艺术讲座
- 04-18全国第二届手卷书法作品展获奖入展公示名单
- 04-13《中国书法报》创刊并面世
- 04-13辽报集团注资合作 中国书法报社在京揭牌
- 04-13《中国书法报》创刊: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 引领书坛
- 03-25福建省老艺协书法委员会在省老干局召开会议
- 10-10首届福建民间文艺“山茶花”奖揭晓 陈友荣获奖
- 04-25世界榜书联合会中国中原创作中心成立
- 标签列表
-
- 中国 (3633)
- 书法 (2438)
- 开幕 (1922)
- 书画 (1753)
- 艺术 (1665)
- 艺术品 (1582)
- 作品展 (1561)
- 收藏 (1357)
- 拍卖 (1322)
- 亮相 (1318)
- 北京 (1297)
- 美术馆 (1266)
- 举办 (1192)
- 组图 (1170)
- 在京 (1131)
- 展出 (964)
- 作品 (914)
- 油画 (886)
- 博物馆 (822)
- 画展 (804)
- 艺术展 (734)
- 市场 (722)
- 画家 (669)
- 当代 (669)
- 文物 (658)
- 香港 (635)
- 艺术家 (631)
- 美术 (623)
- 名家 (615)
- 上海 (572)
- 万元 (564)
- 南京 (469)
- 书法展 (450)
- 画作 (442)
- 首次 (441)
- 国画 (433)
- 征稿 (423)
- 大展 (422)
- 将在 (415)
- 拍出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