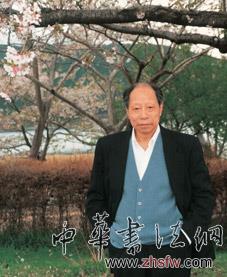首页 > 美术 > 中华绘画 / 正文
| 王伯敏:西子湖畔铸就辉煌 |
| www.taizhou.com.cn 2010年03月05日 10:02:54 星期五 来源:温岭新闻网 |
2004年11月19日是个美好的日子,西湖上晴空万里,艳阳高照,钱江两岸金穗灿灿,硕果飘香。王伯敏先生诗云: (一) 枫叶丹黄树树嘉,一山拟似百重霞。 轻车已过长桥外,回首南屏尽是花。 (二) 西湖彩艇湖心绕,万众倾城笑语扬。 北岸人歌南岸舞,银花天半最辉煌。 这一天,由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员会、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西泠印社主办的“王伯敏教授美术史研究回顾暨20世纪美术史原著·研究文献珍藏展”和“王伯敏教授美术史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美丽的西溪校园隆重举行。 开幕式后,王伯敏教授神采奕奕地陪同贵宾们健步来到艺术楼展厅,这里就连空气里也弥漫着沁人心脾的书画芳香。宾朋们立即把目光投向那座精心排列、无比厚重的“书山”上,有的则走近那些清新山水画佳作,细细品赏着它的高雅韵逸。 在“书山”之上,《中国版画史》系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版画史专著。50万字的《中国绘画史》是建国30多年后才出版的第一部美术史。王伯敏先生介绍说:“1961年4月我同潘天寿先生等出席中央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文化部交给我的任务。1962年3月初稿完成时,文化部组织全国知名专家,在杭州举行审稿会议,会期长达48天。出席会议有大家都熟悉的俞剑华、于安澜、徐邦达、任蠡甫、曾昭燏、潘天寿、史岩、郑为、金维诺、傅抱石、黄涌泉等18人。一审通过后,当年11月文化部又在北京西山召开审议《中国绘画史》二稿会议。”六易其稿,直到20年后才出版发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周扬在听取审稿会议的汇报后说:王伯敏同志是个人才,说明我们对中国美术史研究已有新秀。 由王伯敏担任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计250万字,插图2000余幅,共八册。堪称中华民族上下数千年美术艺术缩影,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里程碑,获国家首次颁发的中国图书奖。有260万字,2000多幅插图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共分六册,亦为王伯敏主编。本书的出版价值,在于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填补了中国乃至东方美术史研究空白。获国家图书奖。90万字的《中国绘画通史》,是王伯敏美术史研究中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他晚年力作《中国版画通史》。这六部凝聚王伯敏智慧、心血和汗水的伟大中国美术史论工程,备受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关注。 参观的教授专家们面对“书山”,无不啧啧称奇,声声道出:“什么是实学?这就是实学。什么是贡献?这就是贡献!”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浙江大学和中国美院的博士生们面对王伯敏教授巨大成就和宏富著作,也一致发出感叹。 来宾们依次参观100余万字的《王伯敏文集》上、下卷,《敦煌壁画山水研究》及由王伯敏主编的《名家点评大师佳作·中国画卷》(获国家图书奖)等48种编著后,接着参观发表论文的期刊和手稿、日记及学术卡片。展出有王先生论文230篇发表在一百多家中外期刊上。他的手稿井井有条地存放在数以百计的纸质盒内,仅1982——20002的20年间撰写的文字就达千万字以上。王伯敏日记中诸如《西行日记》、《敦煌日记》、《茅林寻母记》、《丝路日记》等,几乎每篇都是优美如诗的散文。他的手稿、日记、卡片,每面每行都是那么秀美、流畅,满纸珠玑,令观者得到美的享受。 正如王先生所言:“一个字一个字在我的笔底下流淌出来,而时间也一秒钟一秒钟在我的笔底下过去,只有爱惜光阴,才能完成我的那些作业。”这种坚毅精神和崇高品格,深深打动参观者的心,催人奋进。 在参观的人群中,有两位青年专家学者,看得特别仔细,特别认真,他们是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和浙江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陈振濂,他们仍怀着当年做学生时的情感,仍旧那样虚心,不时向老教授请教。 展览第二大部分,为20世纪各家美术史著作藏本。中国美术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唐代的张彦远是杰出代表,有《历代名画记》传世。20世纪有姜丹书、陈师曾、黄宾虹、潘天寿、郑午昌、傅抱石、滕固、王均初、俞剑华、阎丽川等,他们是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先行者、开拓者。从20世纪中叶开始崭露头角的王伯敏,经过60年孜孜耕耘,终究成了今日中国美术史论方面集大成者。展出中他那些著作,在各家美术史著作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顺理成章,王伯敏自然成为中华文化界美术界公认的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 参观了展览第三部分王伯敏书画作品之后,即使那些平素对王伯敏不甚了解的人,也被这位六史罕人在诗、书、画、印方面的才艺和造诣所折服。 在回顾展和学术研讨会上,主办单位领导许江院长说:“王先生是我的老师……王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家,他是20世纪中国绘画史研究的集大成者。王先生现在仍是我院的在职博士生导师。《论语》中有一段故事,孔子把他的学生比做射手,而自己是驾御马车的御者。如果我们把美术史论比做马车,我们这些实践的人,是坐在马车上的射手,那么王老生正是这伟大马车上的大御者。今天的展览可以说是一位大御者的展览,从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御者的气识和风采。” 主持会议的陈振濂院长,激动地回忆说,他22岁考进美院读研究生时,王教授给他们上第一堂课的情景。他认为王伯敏教授不论在绘画史、书法史、版面史、工艺美术史、民间美术史以及篆刻史方面的造诣都很高,是顶级的专家,甚至可以这么说,在我们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历史学家中的顶级人物,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这样一些大人物,还包括郭沫若。但我说,如果看一看文学,或者在美术史方面,能有什么样代表人物,可以和梁启超、王国维这样的顶级人物相提并论的话,那么,我认为在这一百年以来,王伯敏教授的美术史研究,足可以代表这个时代,足可以使我们感到自豪。 西泠印社副社长刘江在发言中说道:王伯敏老师是我的中国美术史老师。他上课时候认真备课,用实物、图版或照片作直观式教学,引导学生热爱民族传统绘画和对史论学习的兴趣。 刘教授深情地回忆起1961年毕业留校任书法、篆刻课助教时,两家是近邻,常去他家中请教,王老师主动借给他《肖形印臆释》的原稿草稿本,带回家认真细读,并做了笔记,绘录了图稿后,再归还给他。这事给刘江的印象极为深刻。一个搞史论工作者余暇所作的附产品,在出版之前,主动借给一个学印为主的同行去学习应用,毫不考虑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保密,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刘江认为这就是表现了一个教师的高贵品质,愿意帮助学生,引导学生走上专业之路的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 王伯敏学术回顾展,令许多学者频频光顾,留恋忘返。显示了“书山”的无穷魅力。它出于一个学者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热情和高度的敬业精神,不畏艰苦,坚忍不懈,攀登科学研究的高峰,同时也是他爱惜光阴如生命,“莫负光阴”使他获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集大成者。综上“回顾展”让人们感到的是一个“王伯敏现象”,它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那种既平凡又不平凡的现象,把这样的现象展示出来,实在是件极其罕见的美事。 王伯敏从事美术史研究,大量艰苦细致的搜集素材和考证工作,是在广袤千里山野之中进行的。为此,60年来他的行踪遍及神州各地,他登泰岱,上峨眉,过河西,出阳关,云岗击鼓,贺兰觅奇,华山问险,敦煌驻足。王先生有诗云: 治史 治史人怜万里行,西风客里黑沙城。 残碑断处斜阳淡,隐约驼铃似箫声。 在喜庆丰收的日子里,为了能随王先生一同回忆过去那惊魂动魄时刻和快乐日子,作者特意对可亲可敬的王伯敏教授再次进行了专访。王老首先向作者叙述:1962年,我西行至敦煌,莫高窟有500个洞,花了几个月时间对每个洞窟都进行了全面考察,作了详细记录和拍了照片。当时莫高窟还没有修整,也没有人管理,每个洞都是敞开着的,任人自由出入。有一次,当我爬上一个较高的洞窟时,梯子倒翻了,等了好久,仍不见地面上有人走动,心里逐渐恐慌起来。四周荒漠一片,除了风沙声外,寂静得十分可怕。几个小时过去了,才见到远处有一个黑点在移动,我撕心裂肺地喊叫,终于被那人听见,走来帮我扶起梯子,才使我免遭一劫。 1983年我们从拜城去考察克孜尔千佛洞,这些洞窟都散布在悬崖峭臂中间,但我对它产生极大兴趣,想亲自看个究竟。而这时我已经是花甲老书生了,攀悬崖走峭壁显然力不从心,最后由我的研究生用绳索硬是把我拉扶上去。 王老说:那年从乌鲁木齐去南疆,车子从天山的胜利坂上山时,身上穿着背心还出汗,当车子开到海拔4000米时,天色突然阴沉,鹅毛大雪夹着霰子飘飘洒洒,我只得穿上同行为我早准备好的大皮袍。从海拔5000米处的车子走出时,完全置身于冰雪世界,头顶上万丈冰崖晶莹发亮,极目远望,杳漠苍茫,犹若混沌初开,妙不可言。往返一上一下两小时,经历了一年四个季节的天气变化。 王教授还向作者讲了一个有趣故事:1990年冬天,我在广西龙州紫霞洞考察,看见洞内一尊观音菩萨两侧站着十八罗汉,全是世俗歌吹作乐,富有生活情趣。我向管洞老人打听是谁所作,巧得很,作者正是这位管洞老人——林燕高。两人便攀谈起来,林燕高告诉我,他本来是专捏动物的,专长捏猴子。有一次他将几件泥猴带上山来,不断竟引来许多猴子团团围观。消息传开后,远近那些以捕猴获利者都来买他的泥猴去作囮子,果然很有效。一天夜里林燕高梦见一只猴子眼泪汪汪跪在他面前,哀求他以后莫捏泥猴了。林燕高醒来大为感动,从此改塑菩萨,不再捏小动物了。 有一年,王伯敏在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的列车上,利用全部休息时间将考察中的笔记和照片系统整理成册,引起同车厢的瑞士客人的注意:“这位(王伯敏)太专心了,真像日本人。”王先生微笑着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我们向来是这样的。” 王伯敏虽然付出了艰苦劳动和汗水,但让他感到骄傲和欣慰。 王伯敏,1924年11月生于台州黄岩县长浦茅林村,乳名四名。父阮仙全,能吹打、会拉琴。母王梅,善织布。是年茅林遭特大水灾,严冬又遭暴风雪袭击,把这户雇农人家推向绝路。父母为保全这个幼小生命,忍痛将出生才几个月的亲骨肉卖给温岭县城内尚书坊5号王家,改乳名为梅二。养母金二姐,乳母叶凤。这样才在50年后,有王伯敏的《茅林寻生身母亲日记》。他在《长浦吟》中写道: 出卖甲子茅林尽岁荒,洪涛风卷夜苍苍。 伤心儿作幼雏卖,娘自汛澜爷断肠。 思亲年年春夏复秋冬,岁月悠悠断续风。 残梦寻常怜子夜,楼前月冷眼朦胧。 王伯敏6岁入私塾,启蒙老师林子谦秀才赐予学名王伯敏,自幼天资聪慧,举止文雅,好学知礼,勤劳俭朴,深得王家欢心,常随养母远游名山秀水。家庭浓厚文化氛围,良好的启蒙教育和宁静秀美的自然环境,滋润着这颗幼小心灵。11岁作《石夫人图》,次年作诗《登石年岭》:“三月西城外,烟笼岭下川。石牛无介事,日日卧山巅。”课余常摆弄家藏书画,尽情观赏,其中有虚谷的《松鹰》、任薰的《花鸟》、杨伯润的《溪山图》、胡寅的《东坡玩砚》、陈殿英的《棣书》、李藻的《春江》等,这些瀚墨陈香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成长。不久便有《松鹰图》首次参加全县画展,他的《清溪烟柳图》上有长老题诗云:画得云林趣,王郎引兴去。传神数株柳,暮霭写苍凉。 少年王伯敏不仅热衷诗画,对音乐也很有兴趣,特别是七弦琴和琵琶常与他身影相随。并开始背读谢赫的《古品画录》、《古文观止》、《论语》及唐宋诗词。据夏承焘日记:1945年5月6日,过伯敏处,看作画,颇跃然欲学山水自误。夜在陈适处,听伯敏弹琵琶。此时王伯敏在乐清师范任美术教师,夏老应聘在该校兼课。当年第一篇美术史论文《纪元前希腊之画家》在《东南日报》发表。 1946年,王伯敏考入刘海粟任校长的上海美专西洋画系,深得美术史前辈俞剑华的栽培。上海美专的民主自由学术空气为王伯敏成长注入活力,频频在众多刊物上发表有关画史、诗歌、短文。次年美专毕业后,王伯敏马不停蹄北上考入由徐悲鸿任校长兼班主任的北平艺专研究班,又当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受业于唐兰、韩寿萱。12月又备上大红烛、红毛毯,由黄震寰陪同黄宾虹门下,成为虹庐最后的弟子。 王伯敏在北京期间,课余时,他的身心几乎全都沉浸在未名湖畔红楼的故纸堆里,如饥似渴攫取多方面历史知识,同时也受到北大革命传统的熏陶,积极参加北平学生反迫害反饥饿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参观“泰戈尔画展”时,有机会同中国文化界长辈们胡适、徐悲鸿、冯友兰、朱光潜、郑天挺、季羡林等合影,预示青年王伯敏即将步入中国文化界这个壮丽历史舞台。 1948年秋,王伯敏北雁南归,任温岭师范学校国画、语文教员,并与中共浙南游击队取得联系。次年王伯敏边教边从事革命工作,并随革命形势日益高涨,逐渐将工作重心从教学完全转到迎接温岭县全境解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此他被任命为温岭县人民政府首任文教局长,亲自主持中小学学制改革。同年与参加过浙南游击队的文教局同事、善良贤惠的钟定明结为终身伴侣,成了王伯敏事业的最大支持者。岁末辞去局长职务,赴乐清中学任政课教师,但不论形势多么紧张,工作变动频繁,工作忙碌繁重,坚持课余苦读、吟诗、作画、弹琴多种爱好习惯不改。于1952年由华东局文化部直接调入杭州,在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任教,朝夕侍从在黄宾虹大师膝前。 西湖这方圣洁山水,自古就是文人骚客成长摇篮,也是他们展示才华的大舞台。白居易、林逋、苏轼、杨万里等人那些赞美西湖诗篇,早已勒在王伯敏童年的记忆里。他在未名湖立下的雄心壮志,将在美丽的西湖实现,王伯敏心境如潮,久久不能平静。他最初献给西湖的诗: (一) 绿满湖心二月天,碧桃初放柳如眠。 晚来多少春游客,争上苏堤彩画船。 (二) 三月湖头宿雨时,流莺百啭落花轻。 游人水上看山舞,忘了看山画里行。 当青年王伯敏手捧17万字的《中国画史》油印本请教宾虹大师,得“写史要实,论理要明。”八字指点。接着又得诗:“赠王伯敏,黄宾虹年九十。一个瓯山越水人,长年劬学竹相邻。论评南北千家画,君有才华胜爱宾。”爱宾即古代首位中国美术史论家张彦远。 沙孟海曾对人说:王伯敏很有学问根底,冷僧先生健在时,王伯敏那时还年青,我们一起坐在图书馆。张振维说,王伯敏对李杜的诗熟得很,少年时读了,现在都能背。冷僧先生听了,笑着要王伯敏背几首,其用意,似乎有点考考年青人。王伯敏轻松得很,一口气背了杜甫秋兴八首和《野人送朱樱》等五首,又李白十多首诗,冷僧先生当即表示佩服,开玩笑地说,你也是西湖的一个老古董了……所以,做学问,要有根底,王伯敏算是根底蛮深的。 王伯敏在美术学院任教之初,与潘天寿、吴茀之同事于研究室,假日三人常去虎跑探泉,龙井问茶,冷泉亭觅踪。那时虎跑寺谧静而幽深,座落在茂林修竹之中。走进虎跑,如同身处原始森林之境,有心旷神怡,飘飘欲仙之感。潘天寿向同行者讲述他的老师李叔同在虎跑寺出家的故事后,便要王伯敏背诵《病中游祖塔院》和《虎跑泉》。王伯敏操着浓重的台州口音,一口气把苏东坡和黄景仁的两首诗背得如同跑虎泉那般流畅欢快,令潘、吴两位十分佩服。 当时他们三人一起出差去上海博物馆尽览库藏书画精品,潘天寿、吴茀之和王伯敏均各自对所见书画作了笔录。三人又同访吴湖帆、刘海粟、唐云。王伯敏与潘天寿还合著《黄公望与王蒙》。潘天寿情深地作《杜甫诗意图》赠王伯敏。在潘天寿、吴茀之眼中,王伯敏是位可畏的后起之秀。当年那种和谐的同事关系,同游同乐的友谊,令王伯敏至今记忆犹新。 1956年秋天,王伯敏陪同荷兰科学院院士奥古宁游西湖时,首先向贵宾背诵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介绍宋朝的盛况,并向客人讲述西湖十景的由来,原来南宋画院马远、陈清波等人,画了许多西湖风景画,这些山水景画的题名,就是西湖十景的名称。清帝康熙、乾隆南巡时相继书题十景,勒石镌碑成名景,一直延续至今。这位芬兰院士(从事东方美术史研究)盛赞王伯敏学识博大精深,对西湖文化了如指掌。 1957年初夏的一天,午饭后,为了能让王伯敏安静地工作,定明带着三个孩子在杭州饭店前的草地上玩,偶然抬头望见周总理站在阳台上,他慈祥可亲,微笑着两手合掌贴在脸颊上示意让孩子们回去午睡了,孩子们也向总理摆摆手,乖乖地回栖霞岭家中。60年代初,王伯敏出席中央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座谈会,受到毛主席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还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这对正在攀登科学高峰的王伯敏,无疑是一种巨大鼓舞。 1986年10月8日,年事已高的沙老对被评论界称为“琢华夏之璞,写五岳之势”的《中国美术通史》赞口不绝,异常兴奋地对张令杭说:“王伯敏了不起,写出三部美术史。国内没有一位美术史学家已经做了,版画史,中国过去没有过,他首先出版;绘画史,解放以后第一部出版,这都不简单;现在他主编美术通史,大部头,内容充实,规模庞大,超过以前出版的。”不久沙老题写“三史罕人王伯敏”相赠。 这位“一生治史三更月,半世挥毫万里行。”“古稀毕竟犹少,何惧千水与万山。”的学者,是多么雄心勃勃,其意志是多么坚强。十余年后,他竟成为六史罕人!大可告慰师长沙孟海先生。他在西湖畔实现了50多年前确定的宏伟目标,铸就了中国美术史论辉煌。但是,自称世纪一粟的王老并没有停止脚步,由他主编约百万字,5000多幅插图的《黄宾虹全集》将在年内出版。同时还在筹划着《中国岩画史》、《中国边境美术史》的编著。 王伯敏两次受到国条院嘉奖。获三个国家图书奖。省、部级奖项几十个。2004年同月同日(5月 日)同时获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卓有成就美术史论家”和浙江省文联的“鲁迅文学奖”。 王伯敏是中国美院最早的博士生导师。几十年来在他获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也为我国造就一批美术史研究的高级人才,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美好未来奠定了永久的基石。 作者同时也看到王伯敏这个共有17口人的大家庭中,有教授、研究员、编审、高级记者、高经工程师等高级知识分子7人,第三代中有博士生2人。更可喜的是第二代、第三代中都有从事美术史研究的教授、博士们。在编《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时,就有几个子女同时上阵,真是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郁达夫有诗云: 楼外楼头雨如酥,淡妆西子比西湖。 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 最近在西子湖畔柳莺公园与唐云艺术馆为邻新增了一处人文景点,这里矗立着一座颇有人文气息的高大石碑。“相约西子湖”五个朱色行书为邵华泽所书,数百字的碑文由王伯敏所撰。称“相约西子湖,百位画家画西湖”活动,这一盛事是“添湖山光彩,添文化内涵”,意义深远,宜载史册。 细细地品来“相约西子湖”的碑文,让作者想到绍兴的兰亭集序,它们将与湖山共存,名垂千古。
|
- 上一篇:著名画家朱新建因肺癌离世
- 下一篇:习书三味
猜你喜欢
- 2015-03-13 广彩瓷:金碧辉煌潜力大
- 2015-03-13 七旬老人收藏灯具几十种 从一灯如豆到灯火辉煌
- 2014-10-27 刘大为言恭达马书林同书“辉煌中国 共筑梦想”
- 2014-05-26 从苦难辉煌中汲取制胜之力
- 2014-04-16 西藏拉萨:为小昭寺铸就坚实“防火墙” 图
- 2014-04-16 西藏拉萨:为小昭寺铸就坚实“防火墙” 图
- 2014-04-16 西藏拉萨:为小昭寺铸就坚实“防火墙” 图
- 2014-02-20 “继往开来、再铸辉煌”全国书画大展在京举行
- 2014-02-17 北京举行再创辉煌喜迎党的十八大大型书画展
- 2014-02-11 现代画师关良画展首次亮相西子湖畔
- 搜索
-
- 12-02德国的大师艺术
- 12-02八大山人作品赏析
- 12-02诗情画意李可染
- 12-02罕见的晚清名人书法
- 12-02米勒的写实世界
- 10-10福建民俗画大家陈友荣作品欣赏
- 04-14王朔撰文忆亲家朱新建:曾因怕尴尬不想见他(图)
- 03-31四川电视台《巴蜀画坛》:何开鑫翰墨人生
- 03-27邓化鸣携手梦晓为田子坊顾仁源画展作主持
- 03-03走进周鹏飞的书画世界
- 29711℃徐悲鸿生平
- 12196℃陈德宏花鸟画作品欣赏(一)
- 9462℃宋代名家山水画(一)
- 9208℃一尘不染的郑板桥
- 7496℃齐白石花鸟画作品(三)
- 7127℃宋代名家山水画(二)
- 6609℃宋美龄的山水画
- 6541℃吴冠中水墨画欣赏
- 6028℃宋代名家山水画(四)
- 5981℃范曾白描人物
- 10-10福建民俗画大家陈友荣作品欣赏
- 05-27范曾写意人物(一)
- 05-27范曾写意人物(二)
- 05-27王叔晖工笔人物画《西厢记》(16幅)
- 03-10清代名家山水画精选(三)
- 03-10清代名家山水画精选(二)
- 03-08清代名家山水画精选(一)
- 03-07唐寅山水作品选
- 03-07齐白石花鸟画作品(三)
- 03-07齐白石花鸟画作品(二)
- 标签列表
-
- 中国 (3633)
- 书法 (2438)
- 开幕 (1922)
- 书画 (1753)
- 艺术 (1665)
- 艺术品 (1582)
- 作品展 (1561)
- 收藏 (1357)
- 拍卖 (1322)
- 亮相 (1318)
- 北京 (1297)
- 美术馆 (1266)
- 举办 (1192)
- 组图 (1170)
- 在京 (1131)
- 展出 (964)
- 作品 (914)
- 油画 (886)
- 博物馆 (822)
- 画展 (804)
- 艺术展 (734)
- 市场 (722)
- 画家 (669)
- 当代 (669)
- 文物 (658)
- 香港 (635)
- 艺术家 (631)
- 美术 (623)
- 名家 (615)
- 上海 (572)
- 万元 (564)
- 南京 (469)
- 书法展 (450)
- 画作 (442)
- 首次 (441)
- 国画 (433)
- 征稿 (423)
- 大展 (422)
- 将在 (415)
- 拍出 (400)